|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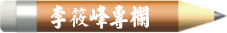
| 莫那魯道 vs. 武士道 |
二月九日,由名導演萬仁所導演的電視影集「風中緋櫻」即將在公共電視開播。這部電影的劇本改編自研究霧社事件有成的民間學者鄧相揚先生的原著〈風中緋櫻〉,是以一九三○年的霧社事件為背景的故事。
行政院文建會為了推廣這部有意義的影集,特別於日前邀約文化界幾位關心的朋友,走訪了一趟事件發生地霧社,並安排與霧社事件當事人的後裔座談。我有幸受邀參加這次的霧社之行。
霧社的山櫻花,在綿綿細雨中,依然固執地燦開著。廬山溫泉的朦朧水氣,馬赫坡的雲靄山霧,又帶引我進入歷史沉思中…。
過去在討論台灣的抗日運動史,習慣將所謂「武裝抗日時期」限定在日本治台的前廿年(1895至1915年),以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為界限。這種分期固然不無道理,但是比較周延的解釋,應該加上「就平地人抗日而言」的前提。因為霧社抗日事件發生在1930年,是在上述的期限之外。就平地的抗日行動而言,噍吧哖事件是最慘烈的一次,但是若與霧社事件相比,顯然就瞠乎其後了。把平地的噍吧哖事件拿來和泰雅族塞德克人的霧社事件相提並論,或許更可以凸顯霧社事件的精神。
容我開門見山地說,噍吧哖事件是一場革命,卻是一場暴虎馮河的革命;但是,霧社事件不是革命,而是一場抗暴,一場視死如歸的抗暴。
噍吧哖事件的主謀者余清芳的革命檄文中宣稱要建立「大明慈悲國」,而且昭告民眾稱,打倒日本後「人民不分貧富一概免稅,也不受法律約束,享有絕對自由。」我曾經問學生,如果真有這樣的政府,你敢接受他的領導嗎?結果沒有一人舉手。
余清芳不僅提出愚不可及的政治空想,更充滿著宗教迷信,例如他說「我埋寶劍於山中,及時拔劍一分長,便可一舉殺敵一萬,拔劍三分,殺敵三萬」,他們拿著傳統的刀劍干戈和宗教法器,要和日本現代化的軍隊對抗,簡直就是清末「義和團」的台灣版。等到日本軍警一鎮壓,起義民眾只好逃竄進入山區,革命不成,只好逃命,最後被捕,以悲劇收場。
霧社事件全然不是這麼一回事,莫那魯道曾在大正初年被安排到日本本土去參觀,他見識過東京的現代化,看過日本的軍校與軍事設施,他知道日本的實力。可是,他為何敢帶領族人對日本在地的官憲如此痛下一擊?他不是在搞革命,他沒有像余清芳講一些政治空話。他們是在外來政權的高壓殖民統治下,受盡屈辱、受盡蹂躪,忍無可忍,最後將生命豁出去,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與其沒有尊嚴的活,不如莊嚴的死。
在我看來,事件之中充滿著「死的哲學」,他們讓欺負他們的日本官憲血濺司令台,但在敵不過日本的高砲、機槍與毒氣之下,他們選擇死亡,不受日本凌辱。他們群起上吊在樹上,去和他們的祖靈契合;花崗一郎以切腹、花崗二郎以上吊,解答了他們兩難的角色;莫那魯道最後進入深山上吊,讓日本人耗費時多日才找到他的屍體。這些死亡的哲學,顯然不是曾被後藤新平譏笑為「怕死、愛錢、愛面子」的一般平地人所能了解。日本武士道中,也有一套死的哲學,但是武士道,碰上了莫那魯道,顯然遜色了!
山櫻花仍在綿密的細雨中固執地綻放著,我想著莫那魯道的死亡哲學,又不期然想到山下那群還在鬥嘴的政客的嘴臉。過去這個外來統治集團講大話要我們消滅共匪,現在卻一天到晚散佈失敗主義、「投降主義」(連戰罵宋楚瑜的用語)、製造害怕戰爭的怯懦氣氛,說台灣人民公投會刺激中共,將引發兩岸不安。他們竟然淪落到可以拿敵人來斲喪台灣人民的鬥志,進而來進行政治鬥爭。這群政客的心態,和莫那魯道哲學,真有天淵之別。
我們不是要鼓勵暴虎馮河的「義和團」心態,但是,今天台灣對外面臨中國496顆飛彈的武力威脅,對內又有舊勢力政客集團在腐蝕我們人民的鬥志,因此,莫那魯道的抗暴精神與死亡哲學,在此時此刻顯得更加有意義。
(http://southnews.com.tw) (2004.02.0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