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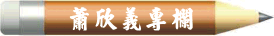
|
祖國臍帶誰剪斷?──台、中關係回顧史 |
臺灣和中國曾有過一段密切的關係。臺灣曾經是中國的勢力範圍、特區、乃至行省。中國近世大變亂時,常有漢人避禍來臺灣,開創新天地。臺灣人口多是漢人移民的後裔〔一〕,習俗文化迄今和中國的漢人尚有類似之處。所以,一般人認為中、臺之間存在著一條自然的臍帶。通俗上所說的「臺灣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強調這種臍帶關係的永恒性。不過,自古的「古」到底是指什麼時代?是三國、隋、明、清初或清末?這是本文想加以探討的一個問題。此外,本文也想探討中臺臍帶的恒固性問題。這條祖國臍帶是否剪而不斷?誰剪過了它?是帝國主義陰謀,家和他們的走狗嗎?把這些問題釐清後,當前中、臺關係的構想是否必須全盤調整?
台灣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這句動聽的口號,幾乎已被當作自明的真理。然而從史實認定的觀點來說,這句口號恐怕大有斟酌的餘地。自古的古到底何所指?
「古」是相對的觀念。對一個歷史短暫的民族來說,二﹑三百年已可算是古了。對歷史悠久的中國來說,總要一、二千年才算得上「古」。所以「臺灣自古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及「臺灣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口號,一般人的印象通常會推溯到隋、唐或秦、漢。
中國近三十年來的歷史教科書及政論文章,多指出早自三國時代,中、臺就已有所交通,隋朝時關係更加密切。盤古出版社的《臺灣──過去、現在與將來》一書的敘述,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公元230年(三國,吳﹑黃龍二年),吳國孫權派遣衛溫﹑諸葛直率數萬人,浮海至臺灣。據現在所知道的資料,這是漢族人最早的大規模到達臺灣的一次,也是中國人民利用先進的文化知識開發臺灣的開始…
公元607年,隋煬帝派朱寬﹑何蠻到臺灣來「求訪異俗」。三年後,又派陳稜、張鎮州率眾萬餘人,從廣東潮州出發,經澎湖到臺灣。陳稜等人初到臺灣,當地居民看到船艦,以為是商人,都去做生意。這證明了臺灣與大陸早有通商貿易習慣。陳稜等人到達以後,派人「慰喻」以波羅檀洞為中心的部落居民;並在臺灣居留一個時期,對當時臺灣的民情風俗﹑生活情況作了調查研究,然後回到福建。隋開皇中,又曾派虎賁、陳稜開發澎湖。〔按《隋書》「流求國傳」以及「陳稜傳」,陳稜的軍階是武賁郎將。史書上寫的是「武賁郎將陳稜」而不是虎賁和陳稜兩人〕。…
唐代對澎湖亦有經營。九世紀初,施肩吾率族遷澎湖墾殖……唐代以後經五代而至宋,因為中原戰亂相循,沿海的漢族漸漸移入臺灣定居。南宋到十六世紀中葉,臺灣和大陸上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聯繫漸密切起來〔三〕。
如果上面這幾段敘述都可靠,那麼臺灣自古就是中國固有領土之說,就有根據了。然而對照史書的記載,上面的故事未免濫用自由心證,和史實相當走樣。
第一、依據《三國志》《吳書》「吳主傳」,孫權派衛溫及諸葛直帶領水軍萬人,命令他們去夷洲和亶洲,「欲俘其民以益眾」(即:俘獲外族人,以便增加吳國的人力)。《吳書》「陸遜傳」和「全琮傳」說陸遜、全琮二人都反對這種侵略行動,但孫權不聽。結果「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四〕。亶洲並沒有找到。夷洲(可能是臺灣)是找到了。「得夷洲數千人還」〔五〕。這樣看來,孫權的軍事行動並不光榮。把這次行動說成是「中國人民利用先進的文化知識開發臺灣」,說得未免太離譜了。一些史論家和政論家把孫權這次不光榮的軍事侵略,當作中國開拓臺灣的證據。這簡直是一大嘲諷。
第二、依據《隋書》「流求國傳」,607年朱寬和何蠻到流求(臺灣)勸歸服隋天子,並沒有成功,結果只「掠一人而返」,次年楊廣再派朱寬去流求慰撫,也沒有人願意歸降。610年,派陳稜和張鎮周率領一萬大軍征伐,結果「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六〕依照《隋唐》「陳稜傳」的記載,陳稜向島民「慰諭」,要他們歸降,他們不答應,於是陳就用武,引起一場激戰。隋軍武器精良,打了一場勝仗,俘獲男女數千而歸〔七〕。把這種霸權侵略的「慰諭」,當作中、臺密切關係的例證。這種曲解,對愛好和平的中國人來說,恐怕是令人尷尬的事。
第三、關於唐代施肩吾率族人遷居澎湖一事,清代以前的文書並沒有記載。清‧順治時的進士杜臻的《澎湖臺灣紀略》才首次記載這個傳說。以後以訛傳訛,連橫在《臺灣通史》「開闢記」也上了當〔八〕。
第四、從唐朝,經五代,到北宋這五百多年,有關臺灣的特別文獻未有所聞〔九〕。南宋趙汝适《諸番志》才打破五世紀的沈默,再度提到臺灣。依《諸番志》,當時臺灣除了和三嶼(呂宋島)進行貿易以外,就沒有其他對外接觸〔一○〕。《諸番志》也提到澎湖島隸屬於福建省晉江縣〔一一〕。但《宋史》卻沒提到隸屬中國之事〔一二〕。《諸番志》的記載只好存疑。
盤古版的臺灣史說唐、五代、宋時,漢人移入臺灣定居。這種說法並不明確。宋時漢人移居澎湖的漸多,但似無多少人移居臺灣島。當時澎湖島和臺灣島互不相涉。澎湖島已成漢人的勢力範圍,但臺灣島還是「蠻番」之地。澎湖變成臺灣的一部分,是1661年(鄭成功征服臺灣)以後的事〔一三〕。
以上簡述南宋以前的大要。以下談元朝以來的主流看法。
元朝末年,在至元年間(1335-1340),元朝在澎湖設巡檢司,徵收鹽稅〔一四〕。這是中國首次在澎湖設置政府機構。明初,洪武帝裁撤巡檢司,並移住民於泉州〔一五〕。自此約二世紀之久,澎湖成為無主之地。到1563年,明朝才復置巡檢司。數年後又廢置。1592年及1604年,分別加強兵員〔一六〕。1622年,荷蘭海軍侵佔澎湖,構築要塞。明朝抗議。1624年,明、荷達成協議:(1)荷軍撤出澎湖島;(2)明朝對於荷蘭佔領臺灣沒有異議;(3)中國保障中、荷通商〔一七〕。
這三條協議值得注意的是,荷人最大的意願是和中國通商。為了這個目的,澎湖遠比臺灣理想。只因中國態強硬,荷人才退而求其次,佔領臺灣。其次,就中國來說,十七世紀初年,澎湖是中國的領土。但臺灣島並不是。中國慫恿荷人佔領自己沒有主權的臺灣島,對中國來說,並不算喪權辱國〔一八〕。因為直到那時候,還沒有任何中國人認為臺灣自古屬於中國,所以荷人離澎佔臺,在中國人眼中是打贏了一場體面的外交戰。
1662年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佔領臺灣,現在史書多稱為收復中華失土。然而在當時中國人看來,卻是增添了新領土。明朝遺臣名詩人盧若騰想投奔鄭王朝的東都,做了「東都行」詩,序言說「澎湖之東有島,前代未通中國。今謂之東番。其他之要害處名臺灣。紅夷築城貿易,垂四十年。近當事〔指鄭成功〕率師據其全島。議開墾立國,先號為『東都明京』云」〔一九〕。
乾隆版《大清一統志》則更進一步說臺灣原屬日本:臺灣「自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國,名曰東番。明天啟中(1621-1627),為紅毛荷蘭夷人所據。屬於日本」〔二○〕。127年後(1871年)所編纂的《重纂福建通志》還保持這種見解〔二一〕。
清世宗(雍正)在1722年即位,下詔曰:「臺灣自古不屬中國。我皇考〔指康熙〕神武遠屆,拓入版圖……」〔二二〕這種看法,在清代是定論〔二三〕。1683年,施琅滅鄭王朝後,臺灣才首次成為中國領土。在清朝領臺二百餘年中(1683-1895),大部份時間都把臺灣隔離開來。《六部處分則例》裡面收錄的「臺灣編查流寓則例」嚴禁人民私自渡臺,必須有官務或商務才可渡航臺灣。渡航時不准攜帶家眷。已渡臺者也不准接眷同住。這個使臺灣孤立化的法規,到1874年才完全撤廢〔二四〕。至此,臺灣才整合於中國本土之內。要說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概從這時才能夠算起。可是21年後,卻把臺灣割讓給日本帝國主義者,如此臺灣成為整合而不可分的一部分,為時才21年,並不是今天通俗見解所持的一、二千年。
本節的史實,對今天流行的「臺灣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句口號提出質疑。但這些史實並不足以做為反對今後中、臺統一的充分理由。統一的實質基礎,最主要的是臺灣的政、經、社條件以及政治文化是否和中國的相融通。此外,住民的意願也同等重要。如果政、經、社、文化條件相容,而且人民願意,那麼,縱使歷史上臺灣並非自古屬於中國,統一也照樣水到渠成。當然,歷史上的淵源,可加重住民接受統一的意願。但在影響統一問題的諸種因素中,歷史上從屬於中國的因素,只是次要的而已。準此而論,沒有長遠統一的歷史並不妨礙統一。同理,有長遠統一的歷史,也不妨礙分別立國。縱使臺灣早在一、二千年前就已成為中國固有領土,如果現代中、臺雙方政、經、社和政治文化格格不入,則統一的基礎也是岌岌可危。
國、共曾經倡導台灣獨立
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者紛紛侵略中國。結果,不但中華帝國從前的附庸國、保護國、朝貢國、勢力範圍相繼失落,連中華固有疆土的一部分也被列強割為勢力範圍或治外法檯地區。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各黨派人士檢討中國近代失土,列出種種清單。孫中山於1924年2月3日在《民族主義演講》中,指出了中國在列強割據下,喪失了旅順、大連、九龍、黑龍江以北、高麗(朝鮮)、臺灣、澎湖、緬甸、安南(越南)、婆羅洲、琉球、暹羅(泰國)、蘇祿群島、爪哇(印尼)、錫蘭、尼泊爾、不丹等等領土〔二五〕。二十世紀上半期各黨派愛國志士大體接受孫先生的清單。1954年,北京所出版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1840-1919)帝國主義割取中國領土圖」,除了增列馬刺甲、安達曼群島(緬甸以南、泰國以西)、阿薩姆、西北大地以外,大致和上面的清單相符合。
這些失土,從近代民族主義者眼中看來,也許該列入「固有領土」的範疇之內。但從傳統中國疆土的觀點來看,則有的是固有領土,有的是附庸國,有的只是數年進京朝貢一次,只算是中華帝國勢力最強盛時,曾與中國維持過外交關係的國家,根本算不上中國領土。臺灣在這一堆「失土」中,究應居於什麼地位呢?當然不會像朝貢國那麼疏遠。多數人常把臺灣和朝鮮、安南並列。從居民的種族看來,臺灣的漢族和中國漢族親近得多。但從歷史關係看來,則朝鮮在悠久歷史中和中國關係最密切,安南其次,最後才是臺灣。瞭解了這個背景,才會瞭解為什麼二十世紀上半期多數中華愛國志士都支持朝鮮、越南、臺灣的自治或獨立運動。
一﹑國民黨鼓勵台灣獨立
國民黨自1943年開羅宣言後,才主張收復臺灣。但在其前,則多主張自治或獨立。早期以自治為主流,晚期則以獨立為主流。依據戴季陶的回憶,孫中山曾於1914年說過他想向日本提出三項主張,其中之一是:「臺灣與高麗兩民族至少限度也應實施自治。」〔二六〕1925年孫臨死前再告訴戴說:他主張臺灣與高麗至少應該自治,各自設立自己的國會及自治政府;他也希望中國能夠獲得完全的獨立。〔二七〕孫先生所說的自治,是指在日本統轄下的自治,而非中國之下的自治。顯然,他並未主張收回臺灣。同時,他相信中國不必收回朝鮮、臺灣,也照樣可以獲得完全的獨立自主,絲毫無損於領土與主權的完整。
孫先生逝世後,國民黨對臺灣的主張從自治轉移為獨立。1926年1月13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把臺灣的「民族革命」和越南、朝鮮、菲律賓的民族革命相提並論。意即國民黨明白贊成臺灣民族獨立。
1927年2月5日,戴季陶在黃埔講「孫中山先生與臺灣」,講完孫先生主張後,戴先生接著說自己的看法。他雖說「臺灣民族即是我們中國的民族,臺灣的領土即是中國的領土」,然而他認為收復臺灣未切合實際,所以不如鼓吹臺灣獨立。他說:在臺灣的中國同胞被日本人壓迫欺侮,就像高麗人被壓迫一樣,因此我們鼓吹臺灣獨立。臺灣的民族獨立運動必須和命運情勢相同的高麗及中國諸被壓迫民族的獨立運動互相聯合,共同抵抗帝國主義者〔二八〕。
戴先生在這裡提起一個重要的觀念,那就是:臺灣人是中國漢族的一支。然而種族雖相同,並不妨礙彼此各自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彼此如能密切合作,必能發揮共同的力量抵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
1938年4月1日,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發表演說,談論抗日戰爭和國民黨的前途。其中有一段這樣說:「總理在世的時候,早就看穿了日本這個野心,和中國所處地位的危險。他為本黨定下一個革命對策,就是要『恢復高、臺,鞏固中華』,以垂示於全黨同志。……總理的意思,以為我們必須使高、臺的同胞能夠恢復獨立自由,才能夠鞏固中華民國的國防,奠定東亞和平的基礎。」〔二九〕
二﹑中共也鼓勵台灣獨立
看了上節所記國民黨鼓勵臺灣獨立,也許有人會罵國民黨沒氣節,出賣國家民族主權。其實,不但國民黨,就連共產黨和無黨派人士,也都一樣鼓勵臺灣獨立。在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人都一致希望朝鮮、臺灣、越南奮鬥獨立,和中國聯合對抗帝國主義者。對於外國人在鼓舞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自救的原則下來提倡臺灣住民自決或獨立,當時中國人不但不譴責其為干涉中國內政,反而視其倡導臺獨就如倡導中國獨立一樣,表現了崇高的國際道義,這個時代思潮,和今日的思潮有所不同。我們回顧史事時,除了透過今日的思潮來評論史事外,更應進一步用當日的思潮來瞭解當時的史事。
1928年4月15日,臺共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中共代表彭榮列席指導。決議案中和本節主題有關的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臺灣民族獨立,建設臺灣共和國;把臺灣民族獨立運動當作社會主義運動的前提;臺灣的民族主義運動,須與中國及其他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互相合作聲援。這些立場得到了中共的支持〔三○〕。
1928年7月,中共舉行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裡面提到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北部的蒙人及回人,東北的朝鮮人,福建的臺灣人,南部的苗人及黎人,新疆的維吾爾人,西藏的藏人等等〔三一〕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僑居福建的臺灣人是被當作具有自己獨特文化的少數民族,如同蒙、回、藏、苗、維、黎等族,而未被當作是漢民族的一支。從民族學觀點看,要說臺灣人是漢部,自是正確之論。但漢族臺灣人在邊陲地區受到中國政府長期海禁隔離政策的疏隔,加上外國文化的影響,逐漸形成與中國大陸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並演變出相異的價值觀念。因此,在文化上兩者同中有大異。所以中國人在當時看臺灣人(包括居住於臺灣以及僑居於中國的臺灣人)為另一個宗族或民族,也是正確的看法。
上述中共第六屆大會對臺灣民族所持的立場,在1928年7月所召開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再度加以肯定〔三二〕。
1928年7月,中共中央委員會所發布的「中央通告」第五十四號,提出要從日本收回山東及滿洲的主權,但並沒有提到收回臺灣的主權〔三三〕。未提及臺灣,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中國自五四運動以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情緒極為高昂,所以要求從日帝手中收回失土,是中國人共同的態度。但中共僅要求收回山東及滿洲。國民黨也一樣。依據Hsiao與Sullivan兩位教授的研究,國、共雙方在四十年代初年以前都未曾想到「收復臺灣」,他們屢次宣告要從日帝鐵蹄下收復的失土,從未包括臺灣。可見,在當時,中國人並未把臺灣當作不可分割的疆土。沒有收復臺灣並不損害中國的主權及領土的完整〔三四〕。
1934年1月,在中華蘇維埃工農兵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評論1931年憲法大綱各條款。他說:「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第十五條保障:為全世界革命工作被迫害而居住於中華蘇維埃地區的無論任何民族,均享有受到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庇護及協助民族革命成功與建立獨立國家的權利。」這個支持民族獨立的政策是正確的。朝鮮、臺灣、安南、爪哇等地的代表都來參加蘇維埃大會,表示這個政策獲得朝、臺、安、爪等外國民族的支持〔三五〕。
1935年8月1日,中共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也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裡面,呼籲所有反對國主義的中、日人民聯合起來,並與被壓迫民族如朝鮮人、臺灣人等聯合為同盟軍,共同抗暴〔三六〕。
「八一宣言」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民和日本帝國境內被壓迫的朝鮮人、臺灣人,以及下階層日本人聯合反抗日帝。如此,朝鮮人和臺灣人是被看作日本帝國內的少數民族。這種看法不但毛派人物,就是反毛派人物也都一致支持。例如毛澤東的政敵陳紹禹(王明)二年後(1937年8月)在一次演講中,也引用「八一宣言」的話,呼籲朝鮮人、臺灣人和中國人同盟抵抗日帝〔三七〕。
Hsiao和Sullivan兩先生認為毛、陳兩先生所代表的立場,其意義重大。毛、陳兩先生及其領導下的人士顯然不承認1895年的馬關條約。依照該條約,臺灣住民二年內如不歸返中國就被當作日本國民。然而,中共領導者卻把「日本國內人民」和「臺灣人」截然劃分,不承認臺灣人是日本國民,也不承認臺灣是日本固有領土。臺灣既非日本不可分割的疆土,也非屬於中國主權之下的領域。臺灣就如朝鮮一樣,是日本的殖民地,都在謀求獨立〔三八〕。
中共一面呼籲中、日、朝、臺人民聯合反抗日帝,一面把朝鮮、臺灣的反帝反殖民的民族及社會革命,歸屬日共指揮。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案,指出臺灣和朝鮮等被壓迫民族,以及日本工農份子,在日共領導下,將開始偉大的鬥爭,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並建立日本蘇維埃。中國革命和日本革命將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一個共同目標的基礎上結合起來〔三九〕。這份決議案是由毛澤東及彭德懷簽署的。
這個決議值得注意的是臺灣民族和朝鮮民族的革命應由日共指揮,而不宜由中共代勞。這就明白提示臺灣並非中國固有領域,臺灣的革命不宜受中國左右。至於臺灣及朝鮮民族將來是否長期留在日本蘇維埃之內?這個決議案並沒有表明立場。不過依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臺、朝只是暫時由日共來領導革命,將來都要各自獲得完全的獨立。〔四○〕。
1936年7月16日,毛澤東在延安會見斯諾(EdgarSnow)。斯諾問:中國人民是否要從日本帝國主義者手中收復所有失地。毛先生回答:「不僅要保衛長城以南的主權,也要收復我國全部的失地。這就是說滿洲必須收復。但我們並不把中國以前的殖民地朝鮮包括在內。當我們收回中國的失地,達成獨立以後,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枷鎖,我們將熱烈支援他們爭取獨立的戰鬥。這一點同樣適用於臺灣。至於內蒙古,即是中國人和蒙古人共同居住的地區。我們要努力把日本驅逐出去,協助內蒙古建立一個自治區〔四一〕。」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做了政治報告:「論新階段──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他鼓勵「朝鮮、臺灣等被壓迫民族」爭取獨立。他呼籲「中﹑日兩大民族的人民大眾及朝鮮、臺灣等被壓迫民族……共同努力,建立共同的反侵略統一戰線」。毛主席認為中國人和臺灣人應該以平等的國際友誼來合作。他把臺灣人、朝鮮人等當作受日帝壓迫的「弱小民族」,他要求和他們互相合作,形成國際聯合陣線〔四二〕。(1949年以前,「弱小民族」一辭通常指外國小民族。1949年以後,偶而也指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在中國境內,漢族以外的民族,通常稱為「少數民族」。)〔四三〕
「論新階段」的立場為中央委員會所支持。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呼籲建立中、日、朝﹑臺人民形成一個反侵略聯合陣線,以抵抗日本法西斯軍閥〔四四〕。
1941年6月,周恩來在「民族至上與國家至上」一文,說明中國力求自己民族國家的獨立解放,也支持其他民族國家的獨立解放運動。這些運動包括:朝鮮、臺灣的反日運動,巴爾幹與非洲民族國家的反德、意侵略,以及印度、南洋等地的民族獨立運動〔四五〕。
中共在初期曾經承諾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自決權。1938年11月以後放棄這種承諾,改而要求少數民族和漢族共同形成中國一個國家,雖然少數民族依然可以發展自己的文化並保持某一限度的自治〔四六〕。如果臺灣被視中國不可分割的固有領土,臺灣地位問題被當作中國的內政問題,則上述的政策轉變必適用於臺灣。這樣一來,臺灣頂多只能享受有限度的自治,而絕不容許再從事任何「民族國家獨立解放運動」了。尤其是在抗日戰爭中談論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問題,更是沒有理由來鼓吹臺灣獨立運動。然而周先生竟然鼓吹了,而且把它放在全球被壓迫民族國家獨立運動的一環之中,就值得玩味了。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不是周先生個人的立場,而是中共一致的立場〔四七〕。很顯然地,那時候臺灣問題還沒有被視為中國內政問題,所以中共對國內少數民族政策的轉變,並不適用於臺灣。
Hsiao和Sullivan兩先生詳盡研究所有文獻後,指出在1943年以前,中共一直把臺灣人民(包括居住在臺灣和僑居在福建省的臺灣人)當作一個和漢族有區別的「民族」。中共把臺灣人當作一個民族,主要是從文化上來說的,而不是從血緣或種族上來說的。在1943年前的文獻裡面,臺灣民族宛如朝鮮民族﹑安南民族一樣,都被中共及國民黨認為應該爭取一個完全獨立的民族國家的地位〔四八〕。
1943年開羅宣言主張把臺灣奉贈中國,國民黨面對這個即將收到的天大禮物,就不再鼓吹臺灣人抵抗日本爭取獨立了。中共倒是還繼續數年支持臺灣獨立運動。例如1947年2月底3月初,臺灣發生了二二八抗暴起義事,《解放日報》就在3月8日發表「支持臺灣獨立」的宣言。臺灣人提出三十二條件,要求:政、經、社改革,不但為中共所支持,中共還提供了六點鬥爭經驗〔四九〕。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2日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據說是中共建黨後民主革命時期最重要的一次大會。七大會議曾刊載一份有關臺灣名號的文件,那是「臺灣等國留延黨員致中共七大大會祝賀詞」。這篇賀詞讚揚中共是東方各民族解放的先驅戰士,過去二十四年中為中華民族解放而鬥爭,同時也輔助了東方各民族的民族獨立及民主自由解放運動。簽發賀詞的「臺灣等國」是臺灣、菲律賓、越南、泰國、馬來亞、荷印、緬甸。
這篇賀詞刊載於1945年5月1日的《解放日報》。中共黨中央機關報到那時候還沒把臺灣看作「應該是中國國內的一省」,而是看作「應該成為一個獨立國」。賀詞中明確地提到中共長期支持東方各民族(包括臺灣)的獨立運動。毛澤東在七大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對國際局勢的分析,和上面這篇賀詞可互相印證。可是現今流傳的毛澤東選集卻把這些分析大量刪除,並竄入一段「開羅會議中將東北四省、臺灣、澎湖歸還中國的決議」。於是,造成了中共在開羅會議(1943年11月)以後即不再支持臺灣獨立的印象。據但了中的研究,中共首次正式提出臺灣主權屬於中國,並決定收回,是出現於1949年3月16日《人民日報》裡面的新華社時評──「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五○〕。
台灣人民的民族運動
這一節的史料比前面二節豐富得多,重大事件也遠較前二節為多,然而多已有定論,所以不必詳細論證。限於篇幅,只簡述要點。
在日據時代,臺灣民族運動以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為主要目標。其方式,在一九一五年以前以武裝反抗為主,以後則以政治鬥爭為主〔五一〕。政治鬥爭的理念上,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曾引起了極大的迴響。民族自決的原則,在日據時代臺灣社會實際運用起來,有數種不同的涵義。較重要的有三種:留在日本勢力範圍內,享受自治的地位;回歸祖國中國;臺灣獨立建國,和中國兄弟之邦維持友好合作的關係〔五二〕。這三種主張都非常普遍。從公開言論的頻率來看,第一個主張恐怕最流行。這是由於日警對後二派言論取締嚴密,所以後二派往往用第一派的言詞來做煙幕。第二派寄望祖國強大後收復臺灣。這一派人士大都沒親眼看過祖國,而只憑胸懷中的一股祖國情思來構築祖國臍帶。無數臺胞滿懷熱情踏上祖國聖地後,才發覺中、臺兩個社會的生活方式及價值觀念已大有差距,在臺時的想像和回祖國後所經歷的實際接不上,因而悵然若失;由此而不能不對毫無保留的祖國心態加以檢討。這種艱辛的心路歷程,不少臺灣作家曾經提出來討論,而以吳濁流、鍾理和、張深切等人的作品最為沈痛感人。
對這種祖國經歷,可能發生幾種不同的反應:打消對祖國的認同;同情中國的處境,但認為中、臺應分別建國,互相合作;仍然認同中國,積極獻身中國的改造。由於當時國、共以及無黨派人士鼓吹第二條路,所以多數回祖國的臺胞就選擇了這條路〔五三〕。
第二次大戰後,臺灣人的祖國情思一時膨脹到頂點。可是由於祖國官僚腐化殘暴,才一年半時間祖國情思就極盛而衰。切斷祖國臍帶這一種心情,成為民間主流思想。臺灣的報刊電臺由國民黨嚴密控制,所以表面上看不出這個主流思想。但民間私下言論,則明白顯示祖國臍帶已很微弱〔五四〕。
結論
從第一節所列舉的史料,我們知道「臺灣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句話,並不是史實的陳敘,而是二十世紀中葉以後才在中國人心胸中新萌芽出來的願望。中、臺之間的政治臍帶並不悠久,也不強固。統一臺灣的理論基礎,似乎不能從「自古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這一個假設做出發點。
從第二及第三節,我們看出二十世紀切斷中、臺間的祖國臍帶的人,並不限於今日普受譴責的「帝國主義陰謀家」和「叛宗背祖」的漢奸。事實上,一生獻身中國獨立自主的愛國運動人士,正有很多人曾經鼓勵祖國臍帶的切斷。在他們看來,獨立自主的臺灣如與中國為敵,當然是很可悲的事。但如與中國為友,互相合作,則對中國的權益,是利多弊少。
以上只是回顧歷史,指出某些目前流行的口號歪曲了史實。但我無意說因為國、共曾經一貫支持過臺灣獨立,現在就非再繼續支持不可。國策可以順著局勢而調整,並不一定要永遠膠固不變。因此我承認中國有權改變對臺政策。我只是覺得應該堂堂正正說明改變的原因,而不應曲飾歷史。
臺灣多數居民在人種上和中國人極為近緣,如果中國內政修明,保障政治及經濟人權,而政、經、社條件又和臺灣逐漸接近,那麼統一的呼聲或許可以受到更多人的重視。經過非常的變局,歷經多把剪刀連續剪斷了歷史上的祖國臍帶,今後的中、臺關係,不能靠「內政問題」這個檔箭牌來處理。回顧歷史之後,我覺得目前有關中、臺關係的構想,有待全盤調整。在調整的過程中,臺灣住民的意向,應該居於樞紐的地位。至於御用史家所裝飾出來的偽史,可當作聊備一格的學說,卻不宜當作左右中、臺關係的準繩。(認識台灣補充教材:歷史篇之H28配合歷史篇第38頁台灣教師聯盟教材研究組編)
本文注釋甚多,尚待補充。
| (http://southnews.com.tw)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