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人創造自已的歷史,卻無法隨心所欲的創造;他們不能在自己選擇的環境下產生,而是直接得到,給予和從過去繼承而來。」(Marx,1978)馬克思以這段話,評論偉大的拿破崙一世「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姪子路易•拿破崙•波拿巴(Louis Napoleon Bonaparte),如何能籠絡並代表各方勢力當上法國皇帝,主要是在一個結構上政經衰頹的亂世,利用其家族歷史的光環、黨派之間的合縱連橫,虛應的建立法國「第二共和」,旋即又以真正想要的「第二帝國」毀滅「第二共和」。
一八四六年以來的法國當時失業率高、工資下降、貨幣市場崩潰、股價慘跌等經濟蕭條現象嚴重;在包括擁護波旁王室的保皇黨派、溫和共和派、社會黨人(左派共和派)、擁護拿破崙王室的波拿巴派,和考量其生存經濟條件與社會連帶層級形成「是又不是一個階級」的農民等競逐權力下,一八四八年十二月,路易•波拿巴獲得廣大農民的支持,以囊括百分之七十五選票的五百萬票當選法國「第二共和」總統,卻又在一年後背叛農民與工人政變稱帝,「逮捕三百名市議員、在巴黎殘殺四百名工人、大動亂、七萬農民與城鎮居民起義、法國三十二個省宣布戒嚴(共一百三十個行省)、兩萬六千人被逮捕、一萬人充軍」。(Sauvigny,Bertier and PinKeny,1989)希冀民主共和的「人民的力量」化為泡影。
馬克思的這本政治社會學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以經典的辯證分析說明了人在政治的開創與限制性質,主要是受到「結構與事件」(structure and event)兩方面力量的過程和交互影響:政治與經濟等結構式問題與客觀現實,會和由人所發動的事件與運動的主觀意圖交織,產生有機的變化;但意圖的行動卻常常產生非意圖的結果。因為歷史的幽魂總是飄盪在結構、人的意識與實踐的天空深處,讓那錯綜複雜的政治權力競逐與社會變化顯得益發弔詭與戲劇化。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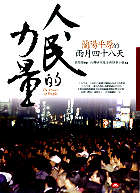 而「人民的力量」在台灣卻曾十分成功的展現,雖然從「黨外」到「民主進步黨」,拉長歷史距離後現在看來,昔日無私奉獻的理想今日也戲劇化呈現傾頹腐敗之勢。 而「人民的力量」在台灣卻曾十分成功的展現,雖然從「黨外」到「民主進步黨」,拉長歷史距離後現在看來,昔日無私奉獻的理想今日也戲劇化呈現傾頹腐敗之勢。
如果說,「權力是對社會有深遠影響的強制性決定的社會能力」(Orum,1989),則我們這裡所研究的,是探究權力如何在社會場域裡被競逐與運作。只不過是從馬克思筆下的法國總統/皇帝大位,轉換為宜蘭地方縣長/省議員的具備「強制性決定的社會能力」的權力追逐而已。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七日,一個選在宜蘭縣羅東鎮鄉下、看來微不足道的地方所召開的選舉協調會議,歷史卻顯示,那現在幾乎被遺忘與淹沒的廣興會議及其在四十八日後所產生的結果,是從台灣的東北部所升起的巨浪,呼應著一九七九年台灣西岸南邊的美麗島事件所在地的高雄呼號,成為顛覆國民黨戒嚴體制,整體黨外民主運動大浪潮的最關鍵性戰役之一;其前後發展過程中,開啟了二十四年的宜蘭綠色執政與民主進步黨的取得中央政權,並且,因緣際會的,直接或間接產出了許多全國性政治人物:林義雄、黃煌雄、游錫堃和陳定南等,他們分別擔任或曾經擔任民主進步黨主席、監察委員、行政院長和法務部長等黨政要職。
然而,在今日弊案頻傳,民怨四起的新政治形勢下,岌岌可危的民進黨政權,似乎陷於一種我們可稱之為「權力的高度均衡陷阱」──政治人口的利益需求高於合理的資源分配現象──使得派系的共生共犯結構傾向,無法在黨政利益與人民期盼間做出理想回應。
首先看出這個問題的人是林義雄,他毅然選擇離開了民進黨;而昔日為清廉、進步象徵的其他幾個人,陳定南爾今罹患癌症,游錫堃續任民進黨主席卻顯得優柔寡斷,建樹有限。這時,這幾年來幾乎算是最為潛沈的黃煌雄,卻由其主持的台灣研究基金會策劃以一本書《人民的力量》,把那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日的記憶重新喚醒,在這曾由黨外主導,人民希望之所託的台灣民主運動風雨飄搖之際,產生了震聾發聵的作用,本質上透過對於廣興會議的歷史回顧,問了一個石破天驚的問題:
「那黨外的無私奉獻精神今日何在?」
三
歷史並非由一個人創造,偉人的精神也是,或許我們該這麼說,是集體意識所匯聚的一群人創造了歷史。但這段歷史由黃煌雄來問這個問題極為合理,雖然之後的二十年,歷史主角似乎轉向擔任更具實權公職的游錫堃等人。
文獻顯示,黃煌雄從一九七○年代後期的助講及巡迥台灣演說開始政治生涯,他這個人曾經擔任過三屆立委、一屆國大代表、一屆監察委員,問政的認真與嚴謹向來被稱為是「立法院的模範生」,但是,他介於「學者」與「政治家」間的個性,在民進黨內總是被視為是不結盟的「孤鳥」、「獨行俠」。而其被「邊緣化」的歷史弔詭,卻在二十年後顯示出其「真金不怕火煉」的價值。
令人不勝唏噓的是,他竟和林義雄一樣,成為現在的民主進步黨少數拿得出來的清廉、進步和有理想形象的人。黃煌雄其堅持原則與理想,給人略顯孤單面向與沈悶印象,有點「古代人」意味的一貫性格,數十年不變;而在當今民進黨一片重拾創黨精神的緊急呼籲中,這書中他的角色,卻又給人與時俱進的樣貌。
我們發現,原來在今日後現代社會中,保持「原則」是一件歷久彌新的事情。而從《人民的力量》書中,雖然出場人物眾多,如果細讀會發現,做為這場會議「關鍵貢獻者」(key trigger)的黃煌雄,究竟怎樣將其力量貫注並贏得這場關鍵戰役呢?那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日的記憶,還需要更多的細緻分析。
四
可以這樣說,從歷史角度來看,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凡是完美的人格就是握有詮釋權力的作者針對文本的美化,會喪失真實性,也早晚會被翻案。所以,近來許多重拍歷史偉人,如電視劇「大漢風」的項羽和劉邦的楚漢相爭、西方電影「亞歷山大大帝」等,均顯露了經典人物的致命缺點和其面對的悲喜劇方式。
如性好漁色、市井粗魯,但為人豪邁能「用人不疑」、有「容人之量」的劉邦,若沒有呂后的節制與道家高人張良戰術上指導,體察社會局勢與民心需求息兵養生,則不可能成就霸業;而剛愎自用卻有著高超品德、真情至愛的項羽,擄獲了天下美人虞姬之心,卻因暴戾脾氣,不能察納雅言,徒有百萬大軍而失了江山。
這些歷史中的人物,啟迪我們的是,除了主觀的意圖外,如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中所言,並且是受制於政治、社會與經濟結構,和歷史的幽靈作用的。因此,若說起《人民的力量》這本書的弱點,就是在於欠缺對於出場人物性格的立體描繪,讀者讀來總是少了那麼一點情感澎湃起伏的故事性,這或許是這些人都還健在的緣故;但其優點卻是,以忠於歷史原貌的「學術式」訪談和敘述,將幾乎隨老成凋零的民主運動重要一頁保留了下來,並且透過當時的場景紀錄,活靈活現的呈現了選舉過程的焦慮、緊張與幽默,從一些細微的部分,也讓讀者見到了所謂無私奉獻的「黨外精神」。如:
「……林和國繼續說道:『我們如果叫你不要選,你會不會硬是要選?』陳定南無奈答道:『當然不能硬選。』林和國於是提議:『這樣好,你剛才說認同我們二十四個代表,現在我請你去選縣長。』『對對對……』與會代表一窩蜂鼓掌叫好,陳定南抱起《六法全書》,不情願的說道:『這不是叫我去做犧牲打嗎?』」
「我問陳定南他過去曾不曾演講,他說不曾,不得了……擔心這場選舉不知道怎樣選下去。在當天演講的過程中,台下的觀眾也不斷提供陳定南演講改進意見。」
「幾位老師也經常親身參與文宣張貼工作,在當時情治單位的嚴密監控下,為避免身分曝光,他們多半是頭戴帽子、身著雨衣,悄悄的進行著這項工作。」
「吃國民黨投黨外……在游錫堃競選總部中,由於便當數量有限,菜色也只能算是尋常,常常不能滿足助選人員的需求,某日中午……整批助選人員,浩浩蕩蕩的走到附近國民黨縣長候選人李讚成競選總部的用餐地點,抵達時,一群人就著桌子,拿起碗筷就開始大吃特吃起來,整桌的飯菜比起游錫堃競選總部便當裡的飯菜當然好上很多,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意猶未盡。之後持續吃了一段時間後,終為李讚成競選總部人士所發覺,面對這一批食量頗大的黨外不速之客,李讚成競選總部頗感吃不消,後來遂將整個競選總部工作人員用餐地點遷移,才總算結束這種尷尬的場面。」
「在一九八一年縣長選戰過程中,當時擔任黨外縣長候選人陳定南競選總幹事的黃煌雄,手上經常有處理不完的大小選舉事務,有一次,黃煌雄跟文宣人員開會討論文宣策略與內容直到凌晨三點,回到家時已凌晨三、四點,黃煌雄的太太吳月娥打趣的跟黃煌雄說:『煌雄,是你在選縣長還是定南在選縣長……』」
從人物的個性來說,以上書中片段所提供的,雖嫌扁平,仍可勾勒出廣興會議這一歷史事件的主要演出者的特色。從馬克思《霧月十八日》所啟迪的研究方法來說,「人物」是創造「事件」的施為者(agency),是一切事情發生的開始。即使有再悲慘的經濟蕭條、社會的戒嚴與動盪,若沒有不滿現實的先行者發出第一聲怒吼,與規劃行動的智慧,則社會結構永遠也不會轉變,世界還是在腐爛,不公義的軌道自我蒙蔽地運行。
《人民的力量》書中的這群先行者:已經是當時在宜蘭惟一一席黨外立委的黃煌雄,是理所當然的有全國性聲望的在地領袖。他對於要把將要選省議員的游錫堃、新參選宜蘭縣長的生澀新手陳定南,和新生代的省議員參選人張川田擺在怎樣的政治層次思考,對於這宜蘭黨外,乃至整個台灣民主運動而言,至為重要。
讀者從書中的紀實敘述可以發現:黃煌雄的考量是拉高到一個全國層級的戰略高度,考慮的是「最大勝選,最小成本」、避免分裂的面面俱到因素,而沒有從在宜蘭縣政治實力消長的一己之私角度思考。可以反面思考的說,如果當時黃煌雄並非從台灣民主運動全局考量,他事實上可以為了保全自己之實力而虛應故事支持陳定南,當一個假的縣長競選總幹事,只讓有地方經營實力的游錫堃當選省議員後收為已用,而發展其蘭陽平原的政治影響力;這點,相較於霧月十八日裡的路易•波拿巴,其以權謀和稱帝私心過河拆橋、殘殺異己,顯得格外「過於理想的」醒目。
黃煌雄其堅持原則與理想,有點前面說過的「古代人」意味的一貫性格,讓他在廣興會議中,堅持主持最大勝選可能、無私避免分裂的大局:陳定南選縣長,游錫堃選省議員,也歡迎張川田參選。以當時的政治實力而言,黃煌雄的決定一言九鼎。雖然競選過程衝突不斷,各方勢力也因忌憚黃煌雄的影響而未敢過度逾越。
但現實是,黃煌雄承襲份量過重的蔣渭水以降的歷史責任感,這少了一份權謀,多了一份品格的決定,我們可說乃其政治性格上「下不了重手」的弱點,讓陳定南崛起,游錫堃壯大;黃煌雄在接下來的二十年於宜蘭的影響力逐步被吞噬,所以轉戰台北縣與中央。而這裡我們要思考的是:「品格」是否是政治場域中的第一原則?還是「權謀」才是?還是兩者必須交互應用?項羽和劉邦的楚漢相爭,劉邦爭得了一時,而今日讓人掬一把同情之淚的項羽是否爭得了千秋?在沒有完美人格的政治人物的今日,當民進黨政權陷入空前危機,「品格」、「清廉」、「道德」和「操守」又被推上政治前線時,《人民的力量》一書所敘述的人物類型,值得讀者深深思索。
五
而從結構面思考,或許更能看出廣興會議的馬克思歷史分析的「意圖的非意圖結果」(intentional-unintended consequence)。從書中我們會發現,在後美麗島事件的第二年,當時整個台灣可以說仍處於風聲鶴唳的肅殺氣息中。全國黨外領袖黃信介、張俊宏、林義雄、姚嘉文、施明德、呂秀蓮等均鋃鐺入獄,現在的總統陳水扁當年是後生晚輩、年輕的辯護律師之一,而政治與社會結構處於保守、恐懼和噤若寒蟬的狀態。
從書裡可以看到國民黨當時趾高氣昂的相信,取得宜蘭縣長與省議員的席次是輕而易舉之事。這事不但國民黨相信,事實上,連當時的黨外所有人,包括領導的黃煌雄,和參選的游錫堃、陳定南,和張川田都心知肚明,勝過擅長打組織戰的國民黨是件非常困難的事。
但正如本書書名《人民的力量》所顯示,宜蘭做為一塊台灣「民主聖地」有其特殊性。就在全國各地因美麗島事件大逮捕而懼不敢言時,曾經在日治時代出現抗日英雄蔣渭水,也於國民政府統治初期產出過郭雨新等黨外先輩的宜蘭,人民反而因為高雄這壓制民主的作為而累積了抵抗的能量。這股能量所等待的,就是不怕死的「揭竿而起」、奮不顧身的「登高一呼」!
這點,我們認為,在廣興會議時事實上並不知道的,或者說是模糊不清的;證據是,從書中描述的當時的各自盤算可以知道:意圖上當時沒有人相信可以當選。如陳定南覺得自己是「犧牲打」、游錫堃力阻張川田參選,因為省議員黨外基本盤不可能當選兩席、當時民眾也曾傳出黃煌雄要出馬選縣長,結果也沒行動;黃煌雄雖從黨外民主發展角度有堅強意志力協調保持和諧,但也必須承擔讓張川田參選後的游系不滿,對於陳定南的輔選勝選也完全沒把握等。
因此,從馬克思的「結構與事件」歷史過程分析方法來看:從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召開廣興會議至十一月十四日的投票日的四十八天,台灣最著名的,時常陰雨綿綿的蘭陽平原的政治局勢,也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轉變。
政治結構上是國民黨已經從二次戰後連續三十年在地方執政,可說是盤根錯節,牢不可破。而整個台灣的社會經濟形勢,也因為美麗島事件大逮捕後,人民雖然政治上有白色恐怖,但是,經濟狀態處於繼續成長、日常生活作息也趨正當的情況。而台灣民主力量之所以能夠增長,以媒體輿論為主體的市民社會得以形成,弔詭的卻是因為人民在經濟上是從生存的滿足朝向生活的追求轉變,衣食足而知榮辱,也要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
而一九八二至八五年間,白色恐怖的箝制亦深入大學校園,我們在台大的學生運動參與,和許許多多的同學產生的集體意識,「那時代的理想青年,憂心戒嚴的烏雲罩頂不知何時解脫的痛苦」(石計生,2006),也做出了校園言論與出版自由的要求,正是這整個大的台灣社會結構轉變下的市民社會先行呼聲。
地方客觀結構上而言: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三日選舉截止登記,創造「事件」的施為者,出場的人物包括一、縣長部分,應選一名,登記三名:李讚成(國民黨)、陳定南、許仁修(無黨籍);二、省議員部分,應選兩名,登記五名:陳泊汾、官來壽(國民黨)、張川田、游錫堃、張文鵠(無黨籍)。而國民黨部分的主導,是由當時的縣長李鳳鳴與立委林坤鐘、國大代表羅文堂與監委許文政、前縣長陳進東和代議長陳進富等三股力量中的諸人操刀;無黨籍(黨外)則單由惟一黨外立委黃煌雄主持大局。
這份領導名單,可以看出一個事實:國民黨因為長期地方執政而產生政治派系的結構功能分化嚴重,所以,想於選後分一杯羹的各股勢力多元而複雜;黨外則因為是新興的政治力量,在林義雄身陷牢獄的情況下,顯得同仇敵愾而相對單純,黃煌雄的指揮與運作效率上相對有效。更重要的是,宜蘭地方因為「民主聖地」的歷史傳統特殊性,則更能嗅及大政治與經濟等結構式問題與客觀現實,從而能和由人所發動的事件與運動的主觀意圖交織,產生有機的變化。
但可見的是,當時黨外的選舉政治並非「菁英──人民」二元施為者,而是「菁英──中間──人民」的集體運作。屬於檯面上的政治「菁英」:黃煌雄、游錫堃、陳定南、張川田等,說實話,除了前二者比較經驗老到外,其他人都屬剛剛嶄露頭角,在與人民之間顯有鴻溝,難以成事;必須依賴「中間」層級的「次菁英」──如黨外志工、中學老師等──的宣傳戰略討論、行動執行與衝突轉圜排解;這些如李清煌等不支薪的黨工,與地方傑出知識份子徐惠隆等的在地無私加入,宜蘭黨外的「空前」團結,終究使得人民的熱情被喚醒。
選舉過程仍然暗潮洶湧,衝突不斷,雖然不應如書中被過分高估其影響力,但事實是,建立在廣興會議價值倫理約束力共識,確實使得「菁英──中間──人民」的三位一體產生「非意圖」連結或共振,終究是讓國民黨在宜蘭經歷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慘敗。
這場精彩追逐「深遠影響的強制性決定的社會能力」的地方權力大戲,其戲劇張力在於「事件」的發生:當黨外的菁英們在宜蘭街頭巷尾,開始散發由競選總幹事黃煌雄設計的聲東擊西的「打破國民黨三十年縣長專賣局面」的陳定南競選縣長的傳單時,當由中央請來的助講團和地方名嘴結合溪南溪北到處演講時,奇妙的化學作用開始了。
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投票前,已經經過多次政見發表洗禮的陳定南,在「菁英──中間──人民」的三位一體運作啟蒙下,終究展現他的個人演說魅力,也看到他日後連任縣長與擔任中央要職的實力。
如《人民的力量》書中訪問稿所述,他邀國民黨縣長候選人李讚成出來發誓不買票做票,去溪北礁溪帝君廟發誓,去溪南羅東城隍廟發誓,對著國父遺像下跪發誓等戲碼,均是宜蘭未曾見過的戲碼,也使得人民從家中、鄰里、學校和工作地站出來了;黨外的演講場子幾乎場場爆滿,擠得水洩不通。
黨外到今日民進黨選舉時所最擅長的「宣傳戰」,在當時看到了驚人的成效,聲勢看漲後,就這樣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日後徹底擊垮了國民黨的「組織戰」。其原因無他,因為當時宜蘭執政的國民黨的貪污腐化已經到了極點,組織早已經僵化生鏽了;而當時形象清新的黨外參選集體,就因為點燃了民眾積壓的對於全國性大逮捕的不滿,與對於宜蘭地方新局的開創熱情,將縣長與省議員政治權力的權柄,第一次不交給國民黨,而是交給當時由黃煌雄所組織、領導的黨外。
廣興會議意圖上勝選的沒把握,選舉的「非意圖結果」卻是黨外大獲全勝:陳定南以九萬零三百八十票當選縣長,游錫堃如願以四萬一千六百三十一票為黨外搶下一席省議員,張川田雖然以兩萬九千兩百一十五票敬陪末座落選,卻也如願累積了政治實力,逐漸在宜蘭地方嶄露頭角,進而成為宜蘭民進黨籍立法委員。
勝選當天,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日終於有了政治上象徵雨過天晴的這一天,如《人民的力量》書中所述,黨外志工和地方知識份子徐惠隆的日記裡記載著:「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晚間勝選時人聲鼎沸的情景,當時鞭炮煙硝瀰漫,助選員一個個走上台上演講並接受歡呼,說出彼時心情,高鈴鴻紅炵炵的臉上滿堆著笑意,邊越過人群邊說著:『倒下去了吧!騙我不懂,選久了,國民黨也會倒下去。』」
六
「黑格爾在某個地方曾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會出場兩次;但是,他忘了補充一點:第一次是做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做為滑稽劇出現。」(Marx,1978)「霧月十八日」,嚴格來說,應是「十八霧月」,按法語習慣,先說日期,後說月份。它指的是法國第一共和八年的霧月十八日,即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是拿破崙一世發動政變,改共和體制為軍事獨裁,取得第一執政頭銜的日子;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路易•波拿巴效法他的叔父拿破崙一世發動政變,使得馬克思在書中就借用「霧月十八」,這個法國共和曆紀元被稱為「霧月」(Brumaire)的日子,做為「政變」的代名詞,並藉以諷刺庸碌的路易、波拿巴的意味。
今日,當我們以這篇長文評論發生於二十五年前的廣興會議與其所激發的人民的力量時,再重讀馬克思經典名言,有著特別深刻的感觸。
歷史的「悲劇──滑稽劇」所引發的弔詭思考在於,前面所述,慶祝黨外空前勝利的話語:「倒下去了吧!騙我不懂,選久了,國民黨也會倒下去。」在二○○五年的宜蘭縣長選舉中,變成了「倒下去了吧!騙我不懂,選久了,民進黨也會倒下去」。
出場兩次的「黨外──民進黨」,第一次是「喜劇」,第二次是「悲劇」。從一九八一年陳定南勝選開始,經歷游錫堃、劉守成等數任執政長達二十四年的「黨外──民進黨」地方政權,竟然又終結在已經擔任過兩屆八年縣長,從法務部長職位辭官執意回宜蘭參選,不願世代交替的陳定南手裡。
三十年國民黨手裡腐化專權的宜蘭地方政權,歷史輪迴的讓人民重新做出了選擇,以選票質疑僵化了的綠色執政、欠缺世代交替決心的民進黨地方政權。但這並不是偶發事件,環伺其地方乃至全國的氛圍,宜蘭地方的社會經濟失業率排行全國前五名,而陳水扁總統政權目前正面臨弊案纏身,貪污腐化的人民嚴厲質疑,連支持綠色政權最有力的中央研究院院長、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也說出「政績有限、弊案不少」的譴責話語。
而昔日無私奉獻的「黨外精神」,說穿了,就是台灣人民對於實現一個理想社會所願意出錢出力、奮不顧身,寄託政治菁英在民主選舉中實踐的精神。從前,國民黨令人十分失望,所以,「黨外精神」就出現了;但是,宜蘭地方的二十四年綠色執政,中央民進黨政權的六年執政,結果卻是令人民更為失望的地方無能發展,中央結黨營私、上下交相利的貪污腐化現象。
民主的可貴在於,可以經由選票的力量讓喪失品格與理想的一方下台反省。我們或許可以重覆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的經典話語:「人創造自己的歷史,卻無法隨心所欲的發生;他們不能在自己選擇的環境下產生,而是直接得到、給予和從過去繼承而來。」以此說明,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日現在成為一個鮮明的印記,過去黨外的「結構──事件」的過程、「菁英──中間──人民」的集體運作,「意圖的非意圖」結果,過去並非完全過去,它會成為一個陰影,一個幽魂,時時纏繞著現在的施為;大凡不能以史為鑑者,面臨唾棄是必然,但其中果有高難度的堅持原則與理想,既能高超品德、又能「用人不疑」、有「容人之量」者,終能再與時俱進的自我學習中,掌握人物本身的價值,伺時而動,融入歷史洪流,在潮起潮落間,與大海共處成為陽光溫暖照耀。(石計生/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 http://www.southnews.com.tw | 2006.11.2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