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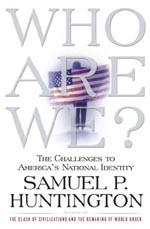 《我們是誰:對美國民族認同的挑戰》 《我們是誰:對美國民族認同的挑戰》
(Who Are We :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撒母耳•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
西蒙和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
2004年5月出版,精裝本448頁,定價27美元。
1993年,哈佛大學政治學者撒母耳•亨廷頓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撰文提出,全球化並不會給世界帶來和諧,相反卻會在不同文明之間引發衝突——這就是亨廷頓著名的「文明衝突論」,它在國際學術界和輿論界激起的爭議至今未休。時隔10年,他將「文明衝突論」的矛頭轉向了美國內部,再次提出轟動性的論點:大規模的拉美裔移民(西裔)使美國日益分化成為「兩個民族、兩種文化和兩種語言」;一場文明衝突正在美國本土上演。
亨廷頓的這本《我們是誰》目前尚未上市,但他在最新一期《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亨廷頓雖然是該雜誌的創建人之一,但雜誌現在的主編和執行主編均為拉美裔)上發表的該書概要已引起美國乃至全球輿論的討論。美國主流報紙如《紐約時報》,著名雜誌如《經濟學家》都對該書進行了介紹和評論。邁阿密的一位評論家甚至呼籲舉行遊行示威,對亨廷頓的雇主哈佛大學和《我們是誰》一書的出版商西蒙和舒斯特公司進行抗議。
我們先來看看亨廷頓此書的主要內容和觀點。
作為一個由移民創建的國家,美國至今仍在大量地接受來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這也是美國之所以能不斷獲得創造力的原因之一。但在亨廷頓看來,拉美裔移民會對美國造成巨大的威脅。
他在書裏提出,現在對美國傳統最迫切而且最嚴重的挑戰是拉美裔移民,尤其是墨西哥人,因為他們往往缺乏融入美國社會的興趣。與幾個世紀以來的其他移民相比,他們難以割斷與故國的聯繫,總是渴望著回鄉探親訪友、甚至參加選舉投票;他們沒有尋求成功、實現「美國夢」的意願,天主教信仰使得他們漠視對物質利益的追求而安於貧困;他們的教育水準落後於其他族裔,大部分人甚至不願意去學習英語,更拒絕接受盎格魯──新教(Anglo-Protestant)所創、代表美國民族認同和政治文化基石的那些基本信念:比如遵守法律、工作勤奮和尊重人權等等。
亨廷頓認為,盎格魯──新教傳統的退化將導致美國國力衰弱,因為在他眼裏,該傳統不僅是美國民族認同的基石,也是它強大的真正根源。這是以往移民所沒有的現象,以往的移民總是選擇主動與盎格魯撒克遜傳統同化。最好的例子是信仰天主教的甘迺迪家族,他們成功轉型為新教徒重鎮波士頓的望族;約翰•甘迺迪還成為了美國歷史上最受歡迎的總統之一。
亨廷頓接著指出,拉美裔移民帶來的這一威脅因為他們的兩個特點而更顯突出。其一,他們的數量驚人。目前拉美裔已占移民總數的大半,超過黑人成為美國最大的少數族裔。而且他們有著在各族裔中最高的出生率,估計到2050年將占美國總人口四分之一。其二,拉美裔移民居住地很集中。比如,到1998年何塞(Jose)已取代邁克爾(Michael)成為加利福尼亞州和德克薩斯州新生男孩最常用的名字。如果此種情況得不到改變,亨廷頓警告,美國很快分化為由「兩個民族、兩種文化和兩種語言」組成的國家!
對於亨廷頓的觀點,一些學者和專家認為言過其實,對之進行了反駁。首先,亨廷頓引用的資料與事實有一定的出入。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布魯克斯(DAVID BROOKS)認為,亨廷頓鋪陳了一套支持其論點的證據,其實拉美裔美國人的同化是個複雜的問題,因為他們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群體,其中受過教育的人輕易地被美國同化了,來自鄉村的人則需要較長時間,但他們的確是在同化。以亨廷頓所說的他們不願意學習英語為例,雖然在一些邊境地區有居民不願學習英語,但整體來說墨西哥裔移民都知道,必須學英語才能出人頭地;他們的第三代中,60%的人在家中只說英語。
其次,亨廷頓以盎格魯──新教來指出美國文化也有失偏頗。布魯克斯認為,雖然毫無疑問美國人深受神學家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和建國之父佛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思想的影響,但維繫美國人的精神卻不是盎格魯──新教,而是一種全體美國人對未來所持的共同觀念(a common conception of the future);對美國人而言,歷史並非是周而復始的,而是可以不斷取得飛躍的;這種精神在拉美裔移民中一樣存在,任何人都能感受得到。
布魯克斯指出,如果美國關閉邊界,不讓新移民進入,將錯失新的動力、新的經驗以及願意為美國的未來奮鬥的新人,這才是對美國信念的真正威脅。
應該承認,在一定程度上,美國存在著亨廷頓所說的現象。《經濟學家》指出,在美國,商界人士出於廉價勞動力的考慮不談移民問題的陰暗面;民主黨則因為移民投他們的票而避而不談,但目前這一波「拉美裔移民潮」的確存在著特殊的問題,它即使不會形成像亨廷頓所說的分化美國的禍害,也是值得認真對待和未雨綢繆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是誰》一書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
亨廷頓於10年前提出的「文明衝突論」固然爭議很多,但9-11和伊拉克戰爭以後的事態發展卻證明他的遠見和洞察力;他這回的「美國內部文明衝突論」同樣充滿著爭議,但應該說,也同樣值得人們深入思考和討論。(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9期)
http://www.southnews.com.tw
2004.04.18 |